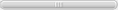叶廷芳:建筑七美

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者安德鲁曾强调,“我要的就是一条弧线”!很清楚,他追求的就是一座没有棱没有角的、与周围建筑“不争不吵”而形成“反差”的建筑,以避免跟“有棱有角”的人民大会堂、天安门等建筑去争锋。
六 反差美
在传统的审美概念里,特别是按照欧洲古典主义的美学原理,“谐调”是一条重要的原则。但这条原则早在17世纪就被突破了!20世纪以来,“不对称”更成了现代美学理论的一条新的原则。
性质相反或形象殊异的两个事物构成审美效应是根据哲学上的二元对立的命题而成立的。所以追求反差美的文学、艺术作品在现代主义兴起以前就存在了。例如在欧洲,早在17世纪,在巴洛克审美风尚流行的中、南欧地区,在当时涌现的“流浪汉小说”中,身份卑微而心智高超的“流浪汉”总是与身份高贵却行为愚蠢的人物周旋在一起;难怪在《堂吉可德》中那位又高又瘦的吉可德先生偏偏与又矮又胖的桑科·潘扎形影不离;后来的浪漫主义继承了这股遗风,于是在雨果的笔下我们看到了那位美丽非凡的女主角艾丝米拉达又偏偏与那位奇丑无比而心地善良的男主角夸西莫多难解难分。在绘画中则是崇高与卑下、圣爱与俗爱、美景与废墟、黑与白等等并置于一图;后来我们还看到早期印象派马奈那幅题为《野外的早餐》的名画——衣冠楚楚的男士们与一位一丝不挂的裸女一起席地而坐。不过这类现象那时多半见之于文学和美术作品中,建筑中虽然也能举出一些例子,但那都不是出之同一作者(建筑师)的统一构思。例如圣彼得大教堂的主体建筑是古典式,而内部的主要装饰出之于贝尔尼尼之手,是巴洛克的;而主体建筑与其大门前巴洛克椭圆形广场(亦为贝尔尼尼设计)也形成不同风格并置的景象。再看法国的凡尔赛宫,它的主体建筑是古典主义的,但它的后花园布局以及某些内部装饰,尤其是华丽的镜廊却是巴洛克式的。这类现象在当时是“违规”的,只是欧洲古典主义的官方总代表路易十四偶尔也未能经受住巴洛克这位泼辣“美女”的诱惑才发生这样个别的事例。但在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的“后现代”思潮兴起以来,建筑中追求二元反差美学效应的现象就频频出现,并日见其多了!
较早进入人们视野的这类建筑当推耸立于柏林市中心的那座新旧并立而又风格迥异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这本来是19世纪末威廉皇帝二世为纪念其父威廉一世而建造的、近似于哥特风格的新浪漫主义建筑,高113米,二战中毁于战火。战后,即1957年,人们想按原样修复它。但承担这项设计的建筑师埃冈·埃伊尔曼却没有铲除废墟,也没有按原样重建,而是聪明地保留了它所剩的71米高的主体残躯,作为战争的警示,而在它的一侧新建一座几乎与它等高的多边形的筒式建筑与之并立,作为新教堂的象征;另一侧再建一座二十来米高的空荡荡的大厅作为功能性的教堂,用作信徒们的祈祷,从而鲜明地反映出两个时代的不同建筑理念。尽管起初充满了争议,但后来越来越受到赞誉。另一个事例发生在20余年后欧洲另一个大国的首都巴黎。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应法国总统密特朗之邀负责卢浮宫扩建工程的设计。贝氏几度奔赴巴黎,考察场地,并反复琢磨:如何在这三面古典建筑环抱的有限空间内插入一座新的建筑?最后决定以反差的美学原理处理这一空间难题,即把功能性建筑引入地下,而地上只占一个入口的地面,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住了新建筑对古典建筑的挤压,而且门面建筑采用钢骨玻璃结构,排除了砖石、水泥等建筑材料的利用,这就虚化了建筑的物质性,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固有空间的广度和亮度。而其门面采用金字塔造型更是一个天才灵感的产物:金字塔乃是人类四大古文明之一的埃及古文明的象征,而卢浮宫内就藏有丰富的来自埃及的古文物,这一门面造型就恰好是卢浮宫这一重要内涵的透露。
然而,正像文学艺术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审美现象刚刚出现的时候,几乎都伴随着一阵大喊大叫,贝氏玻璃金字塔以及70年代诞生的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也不例外。但是,凡是天才智慧的产物往往都具有征服力,故随着时间的推移,束缚着多数人的审美惰性渐渐地被化解了,而变成一片叫好!这一审美经验虽然无法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域移植,但它的遭遇却有一定的规律性。君不见20年后,当北京的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刚公布的时候,也立即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甚至有数以百计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49名院士)联名上书中央,试图依靠行政力量来推翻这一业经专家评审委员会通过的设计方案。他们主要的反对理由是该设计与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等建筑“不谐调”!这些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学富五车的知识里手可惜在现代审美领域失语了!殊不知,欣赏现代艺术或建筑,不仅需要知识,还更需要实践和体验。我说过:一个经常接触现代艺术的出租司机和一个很少涉猎这一领域的科学院院士,在对同一件现代艺术作品或建筑发表意见的时候,我相信前者的见解可能比后者要在理!是的,在传统的审美概念里,特别是按照欧洲古典主义的美学原理,“谐调”是一条重要的原则。但如前所说,这条原则早在17世纪就被突破了!20世纪以来,“不对称”更成了现代美学理论的一条新的原则。这是1970年分别在罗马和威尼斯举行的两次跨学科的国际学术会议得出的共识。难怪,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者安德鲁曾强调,“我要的就是一条弧线”!很清楚,他追求的就是一座没有棱没有角的、与周围建筑“不争不吵”而形成“反差”的建筑,以避免跟“有棱有角”的人民大会堂、天安门等建筑去争锋。因此安德鲁的这一条“弧线”实际上成了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建筑理念的分界线。从现代建筑学角度去看,安德鲁用这一条弧线,也就是用反差的美学原理来处理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附近的空间难题是可取的,它体现了建筑学在“后现代”语境中形成的一个新的理念,即“对话意识”:首先在态度上它既尊重古人或他人的既定存在,同时也不掩盖自己的时代标记和价值取向;其次在行动上它对前人或他人在体量、高度和色彩上不采取“争”的架势,而表现出“让”的姿态。上世纪末德国科隆大教堂近旁新建的一座二层楼的艺术博物馆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我国近年来诞生的国家体育场即“鸟巢”身边“低矮”的“水立方”游泳馆也是设计师自觉之所为。
在国际上,所谓“后现代”建筑的最近表现是兴起一股“嵌入式”建筑的思潮,即在传统建筑中插入一座其风格与原建筑毫不相干的新建筑,有的从外面“开膛嵌入”,有的则从“腹中撑开”。前者如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即为有名的一例;后者如柏林新改建的德国国会大厦中的议会厅及其楼顶耀眼的“玻璃罩”堪称典型。这类现象在小型建筑改造中更不乏其例,近年来笔者在中欧一些国家如德、奥、瑞士等国就目击过不少。其实在我们国家现在也不少见。如北京大学燕南园56号,原是一幢教授别墅,现在在保持外观不变的前提下,被改造成一座明亮、别致而实用的艺术学院的办公室,采用的就是“挖腹换脏”式,广受好评。现在北京古城内许多有年头的住宅或四合院的改建,采用的多半是这种方法。
(编辑:苏锐)
| · | 越界的启示——浅析叶廷芳美学研究特色 |
| · | 《四川好人》改编《江南好人》“异域”与“土著”的嫁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