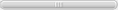当代诗歌生态的“场”和“场子”
○一个诗人最大的幸福是直接面对诗说话,但现在我们和诗之间隔着太多的东西,隔着时代、资本、传媒、评奖,诸如此类。这些东西本身无所谓恶意不恶意,却迫使我们一再远离诗。我不能说这是某种劫持,因为我们并非别无选择。
○精神和人格的分裂,精神内部的分裂,早已成了当下诗歌生态最不可回避的病征之一。诗人的病和时代的病,从一开始就互为表里地纠缠在一起。
○没有了更高的道义维系,“场”就成了“场子”,就到处充斥着“我的小说”,“我的诗”,“知音”就退化成了“知我”,甚至更低。
○当他那几乎称得上微弱的声音克制住并穿透周遭的喧哗,如同一枚枚闪亮的钉子播撒出去的时候,你会想到那根本不是某个人的声音,而是一个场的声音,是场本身在发声。
诗歌的大生态与小生态
关于当代诗歌的生态问题,大家已经谈得非常多了,还可以谈得更多,谈不完。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一是尽可能中性地描述和分析,二是立足诗歌的价值诉求。现在的情况是二者纠缠在一起,有点乱。乱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当代诗歌生态的特点就是乱,而我们的讨论本身就是它的一部分,甚至是一个表征。对我来说,所谓“生态”有大小之分、内外之别,界限不必泾渭分明,但重要性大不相同。对大的、外在的诗歌-人文生态,我们除了领受,更多恐怕只能充当观察者、评论者的角色:它的盲目、自在、复杂性,足以支持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比如最好的时代和最黑暗的时代,因为角度不同。唯有和个人密切相关的小的、内部的生态,是我们可以着力之处,可以通过自觉的努力参与改变和建构,如果这些改变和建构作为某种必要的平衡,还能多少影响到大的、外部的生态,那就谢天谢地了。
我们讨论诗歌生态,是因为我们知道诗对生态有特别的要求,是因为目前的诗歌生态让人感到不舒服,有许多伤害诗的东西需要共同应对。我们的讨论能改变什么吗?显然不能,至少不能指望。诗歌生态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和整个文学的生态、文化的生态以至社会的生态密切相关,许多发生在诗歌领域内的现象和问题,都有更深广的社会和文化根源,包括一系列软性的观念因素,也包括一些硬性的制度化因素。它们自行其是,不会在乎我们的讨论。好在我们也可以不在乎它们,但我们自己的目标应该清楚。对一些性质恶劣的事件表示义愤是一种正当的反应,说来说去一肚子牢骚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做一些具体的研究,尽可能搞清楚其根源和机制,或许更加可取。我们确实有理由搞清楚这些,因为没有人愿意像自然地呼吸那样,吃毒饺子,喝三鹿奶粉。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比较理想的诗歌生态,都希望这生态能让诗人们感觉舒服一点。但这个时代会让诗歌、诗人舒服吗?会有谁为诗歌预备下一个这样的时代吗?我也不知道什么时代让诗歌舒服过,可能是唐代吧。然而近现代以来,诗歌和时代之间却似乎越来越格格不入。就当代而言,我们曾不得不面对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垂直支配,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还曾有人欢呼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降临了,那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它对我们的生活,特别是诗歌意味着什么。
一个诗人最大的幸福是直接面对诗说话,但现在我们和诗之间隔着太多的东西,隔着时代、资本、传媒、评奖,诸如此类。这些东西本身无所谓恶意不恶意,却迫使我们一再远离诗。我不能说这是某种劫持,因为我们并非别无选择。清理、穿透那些把我们和诗隔开的东西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自我反省、自我加持。比如诗人黄梵说的言清行浊,这个问题就值得我们深刻反省,事实上,精神和人格的分裂,精神内部的分裂,早已成了当下诗歌生态最不可回避的病征之一。诗人的病和时代的病,从一开始就互为表里地纠缠在一起。
面对大环境、大气候我们更多地会有一种无力感、无助感,但致力于小环境、小气候的改善却大有可能。很多这方面的有识之士办过民刊,为什么要办民刊?不就是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小环境、小气候吗?抗衡、影响、改变大环境、大气候必须依靠历史的合力,但作为一个内部的生态空间却有相对的自足性,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活得干净一点,舒心一点,可以更多地亲近诗,对诗说话,感受到与诗的直接关联。要建立和葆有这样一个空间需要一些基本元素,而我们并不缺少这些元素。比如友情。保罗·策兰有一句诗,大意是说写诗对他而言相当于从生存之海中透气,对友情我也愿意用这样的比喻。友情也是一个生存的透气孔,和文学之间、写作之间存在一呼一吸的关系。像围棋一样,有这两个“眼”你就能活。我相信让我们聚在一起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正是友情。它不仅是一种自我加持的力量,还是一种互相加持的力量。问题是什么样的友情才能成为这种加持的力量呢?
(编辑:竞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