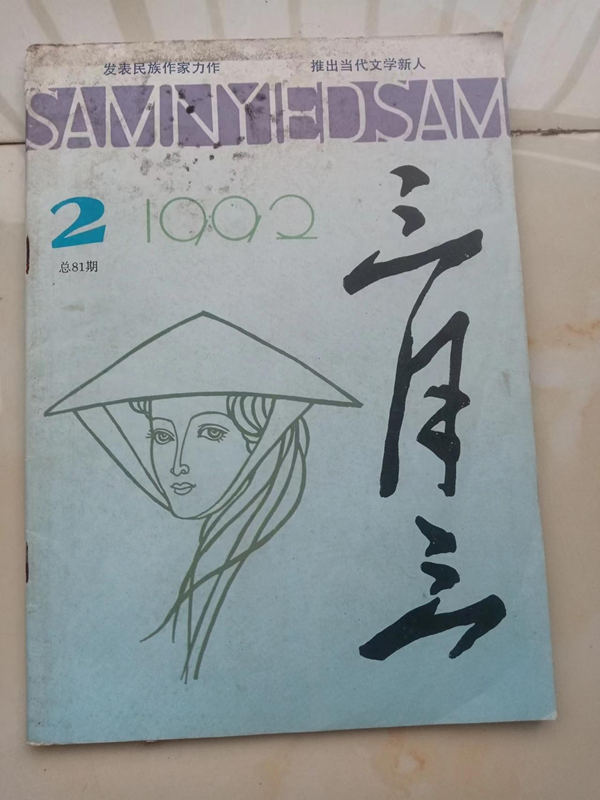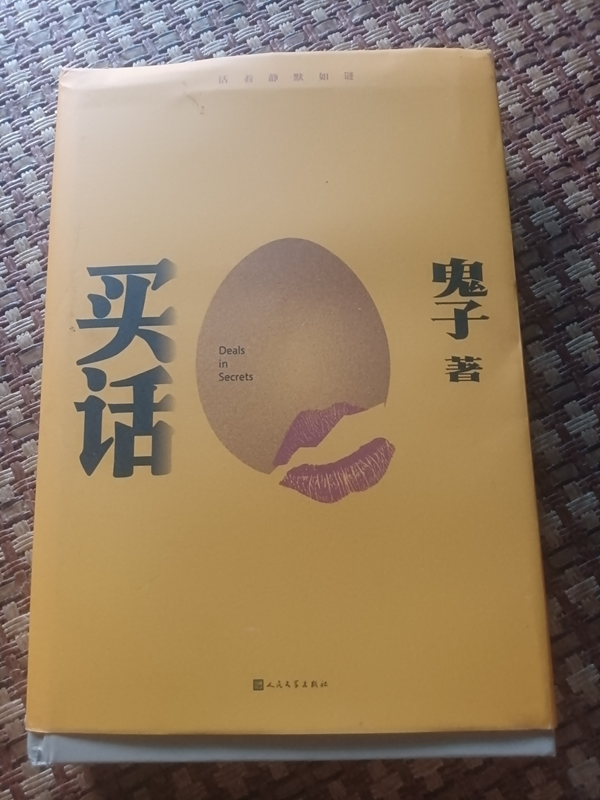鲜活的乡村叙事
——读作家鬼子长篇小说《买话》
品读《买话》这部作品需要耐心和静心。这部小说,说实话,我第一次阅读,看到第四页就想放弃了。好在那时不断提醒自己,这部由作家鬼子用18年写成的作品能够在《十月》和《人民文学》上发表,肯定“有料”。结果越读越有味,连续用了两天时间,一口气把《买话》看完,既在书中无处不在的苦难中艰难跋涉,也尽情享受阅读过程的快感。
沉寂多年“放大招”
最早认识鬼子,是在书上。1992年3月5日,第2期《三月三》发表了鬼子小说专辑,《家变》《火眼.棍子》和创作谈《两点感想》,还有一个长长的鬼子创作目录。
因为“鬼子”这个名字起得怪,又是在同一本书上看到他的作品,并且在他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主任时,我还任过副主任,好像有那么一点缘分。
在往后的日子里一直关注他的作品,他发表的作品几乎每一篇、每一部都认真拜读——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被雨淋湿的河》,以及《一根水做的绳子》《苏通之死》《遭遇深夜》《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瓦城上空的麦田》等作品。他的创作既有实践深度又有理论高度,鬼子本人也和东西、李冯并称广西文坛三剑客。他们三人各有各的精彩,成为支撑广西文学“新桂军”最重要的力量。
我最后一次阅读到鬼子的作品,是2006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鬼子小说》。他总是把小说的触角伸入到底层人物的心底,把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对理想的追求和尊严的满足构筑在苦难的土地上。而《买话》则延续了鬼子对苦难根源的追踪,既有鬼子擅长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和浪漫主义的构思之间寻找一座桥梁进行联通的探索,更有沉寂多年后,对城市和乡村现状睿智的思考,显示了一流作家的沉稳大气、从容不迫。
《买话》中的刘耳带着衰老的身躯回到故土,讲述的是刘耳不为人知的秘密。苦难的形式既有乡党不同命运的书写,又有刘耳在村中被孤立的精神折磨,更有村中不利于刘耳的各种漫天传说。桩桩件件砸向刘耳,他成了“罪犯”,全村人都可以用私刑或者在公开场合“审判”他。他的孤独无人诉说,他的故乡已经不复存在。
这个刘耳,就是作家鬼子用18年的时间经过无数次修改,奉献给中国当代文学群像中的一个耀眼的人物。《买话》对中国乡村的书写,无疑在这一类乡土作品中属于上乘。
《买话》写尽了一个群体的无奈和尴尬
鬼子的《买话》,剖析了刘耳这一代农村走进城市之人的窘境,身体和灵魂没法在城市找到归属,回到农村也找不着北,处处是尴尬和无奈。刘耳的尴尬和无奈,正是当下我们很多人要面对的尴尬和无奈。而这样的尴尬和无奈如何消解,那是文学要持续努力的广阔天地。
都说千里万里走不出故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但刘耳回到故乡,却活成了孤魂野鬼。走进他家大门的,只有疯子香女,还有想从他手里借点钱好续回自己大鸭的未成年人扁豆。刘耳每天与养在家中的一只小白鸡对话,心事只能向小白鸡诉说。当不见了这个伙伴,便魂不守舍,四处乱窜想将自己的知音找回来。若要知道村里人的一些想法和行动,只能“买话”,出钱收买未成年人扁豆的信息。整个瓦村没有一个正常人和他说话,没有人搭理他;他不停地送出茅台酒,一直想和村人改善关系。村人茅台酒吃了不少,但就是没有听到一句真话。
读着刘耳在村里的种种尴尬和处境,不禁让我们发出灵魂拷问:刘耳只是单一的一个人吗?不!他象征着所有从农村走进城市回不了故乡的一群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一批批地离开了故乡,走进了城市,成为了“城里人”。他们为城市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但他们却没法融入城市,他们的根还在故乡。每当清明节和春节到来的时候,在通往乡村的路上绵延不绝的轿车和摩托车队就是他们回故乡寻根的过程。
植物没有根,转瞬即枯萎;人这一辈子如果没有根,走到哪里都是漂泊。寻根问祖、追本溯源是每一个中国人一生都在做的头等大事。而刘耳的寻根并不顺利,并不是村庄变了,而是人心变了。
村庄和刘耳都各有自己不能诉说的苦难,而这正是鬼子的高明所在。用当代文学家丁帆的话来说,就是“《买话》在人性的拷问上更具有时代性,也更有深刻的哲学意蕴,这是一般乡土小说作家难以企及的境界——思想的烈度足以震撼文坛,且是从形下到形上,再到形下二度循环的艺术化抒写。”
瓦村人和刘耳经历的那些隔阂和误会,还能够和解吗?鬼子通过一场“老大人”的葬礼,看似是和解了。在那场葬礼中,局外人刘耳从试探到慢慢靠近,不但献出了自己心爱的小白鸡,还通过努力争取,赢得了“老大人”的认可,不仅成为了死去竹子的老公,也成为了“老大人”的女婿。
读着这个情节,我热泪盈眶。刘耳和故乡重续前缘,重建血脉,正是《买话》给所有读者的希望。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原二级调研员,图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