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平凹近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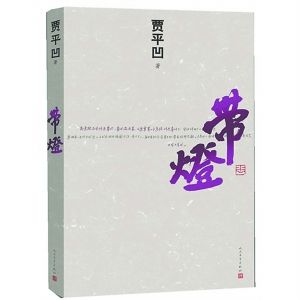
《带灯》封面
阅读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心里时常会产生巨大的困惑。近日读完贾平凹的新作《带灯》,失望地看到作家仍坚持“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秦腔》后记),并以为这种写法类似巴萨的足球,“那繁琐细密的传球倒脚不就是写作中靠细节推进吗?”(《带灯》后记)从40万字的《秦腔》纷乱的线索、人物,到36万字的《带灯》仍然烦琐的生活实录,作家离艺术的想象越来越远,离生活的地面越来越近了。
题材的突破与生活的偏见
《带灯》遵循了作者一贯的写作原则:写作必有原型。这次的原型是作家结识的一位山区乡镇女干部,负责综合治理。带灯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作品中,都是作家心目中一个“可亲可敬”、“高贵”、“智慧”的人物。写农民、农村工作者的善良天性曾让贾平凹早期作品充满人性的光辉,善与恶的纠葛也是他组织情节的重要方式。天狗(《天狗》)、秃子(《商州》)、小月(《小月》)等人物形象成为新时期文学画廊中醒目的画像。带灯这个名字本身就有着光明的意味。带灯原先叫“萤”,因为读到书中有“萤生腐草”的说法,心里别扭而改叫带灯。小说结尾写萤火虫落到了带灯的头上,肩上,衣服上,“带灯如佛一样,全身都放了晕光”。可见作者几乎把带灯当作人世间拯救苦难的佛来写的,她“火焰向上,泪流向下”,如萤火虫般把生命的光亮奉献给他人。可全文除了结局时突兀地给带灯添上这个辉煌的尾巴外,其余有关带灯社会生活事件的叙述则平淡得近乎板滞,细碎得几近无聊。带灯区别于周围人的小善良、小清高、小文艺才华都不足以改变她乖顺听话、随波逐流的基本性格特点,她的美涣散在每日应付的工作中、淡然寡味的生活中,涣散在作家对现实秩序有意识的迎合中。
带灯综治办主任的身份,一方面是作家写作题材的突破,基层干部第一次成为贾平凹作品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使作家站在新的立场审视普通农民,农民形象在这部作品中遭到贬抑。和许多写实派作家一样,贾平凹自觉地承担了为一个时代代言的责任,他把这种“自觉跟紧时代脉搏”的意识叫作“现代意识”。贾平凹说:“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而地球上大多数的人所思所想的是什么,我们应该顺着潮流去才是。”(《带灯》后记)文学的现代意识在这里等同于对时代的干预、对当下生活的焦虑,现实生活取代了艺术作为“某种纯属形式的东西”(尼采语),生活的偏见削弱了作家对民众更为高尚的关怀。
农民形象的塑造
《带灯》中上访的农民成为社会矛盾的重要制造者。带灯最重要的工作是阻止农民上访。在带灯眼里,那些老上访户就是农村的刺儿头,他们不安心生产,把上访当作便捷的谋生之道,对一些明明解决了的问题还纠缠不休。带灯把他们看成可怜又令人生厌的脓疮,摆也摆不脱,挤也挤不掉。王后生就是这样一个吃上访的专业户。王后生第一次出现在樱镇政府大院时,口袋里装着两条蛇,他一边玩着蛇一边把书记堵在办公室倾听“群众的呼声”,结果被带灯用棍子敲了手。他鼓动从大矿区打工回来得了肺病的人上告,“每家给他两百元钱,他负责去告,将来告赢了,国家给了救济款每户抽给他两千元就是了。”带灯质问王后生:“你怎么变得这么坏呢,让人恨你!”带灯对上访者说:“你们是不是觉得政府是唐僧肉?”“如果把上访当作发财的途径,那你们就上访吧。”这些上访户是自私、贪婪、狡猾、不顾脸面的泼皮无赖,而不再是令人怜悯的弱势群体。
从《浮躁》开始,贾平凹不再倾心于塑造商业时代的英雄,而是对被金钱腐蚀的人性进行批判。如果说《废都》时期作者对变革后的社会乱象还表现出无奈的心境,那《带灯》中作者对农民中的暴发户则表现出露骨的痛恨,他把这些先富裕起来的人看成抢占社会资源、为富不仁的黑恶势力。元家五兄弟是樱镇的豪强,要办大工厂的消息传出后,元家五兄弟抢占河滩开沙厂,协助镇政府搞搬迁,是帮助官员处理“不听话”群众的黑手。薛家兄弟在大工厂建成前就收购老街的旧屋,等着大工厂建成后把老街改造成一个集餐饮、商业、娱乐一条龙的服务中心。看到元家沙厂挣钱,薛家也疏通关系办了另一家沙厂,两家沙厂的恶性竞争最终引发了两个家族的群体斗殴事件。元、薛两家带着资本原始积累时噬血的特性,用他们的精明、强悍、凶暴不知餍足地攫取财富。
宗教感缺乏与男性写作
夏志清批评中国现代文学肤浅,因为没有像托尔斯泰、莎士比亚那样“借用人与人间的冲突来衬托出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作家正视人生问题时内心缺乏一种深刻的宗教感。这样的认识同样适用于中国当代文学。贾平凹虽然总在强调“实录”生活,但他单一的价值判断只能将人物分成善与恶、是与非两类,这造成了他的小说“难以摆脱视域上的单一性,带来人物、故事上的重复”。(洪子诚语)
同样在主人公带灯这个形象的塑造上,贾平凹没有将带灯生活的矛盾放到樱镇这个矛盾纠合体中,政府工作者身份让她成为樱镇人敬畏、巴结、羡慕的对象。带灯分裂的生活源于她自己对生存状态的不满——美丽的外表、大学的文化、小资的情调都让她从精神上远离樱镇那些“带虱子的人”。贾平凹说“环境的逼仄才使她的想象无涯啊!”这个无涯的想象来自带灯对从樱镇走出去的作家、官员元天亮的爱情幻想,她不断给对方发上千字的“短信”表达自己狂热的爱恋。
《带灯》发表时贾平凹刚过六十,他希望新作能有西汉文章品格,向海风山骨靠近,用意直白,下笔肯定。比照带灯的现实与幻想两种生活,作家运用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笔调写,前者用枯笔,后者则回到以往浪漫、灵动、华丽的明清文风。带灯对元天亮放弃自我、甘做“秘书、书童、阳台上的花草、桌前的小猫小狗”的爱情让我想到《废都》中围绕着庄之蝶身边的文艺女青年们,她们爱情产生的唯一缘由是这个男人拥有令人渴慕的地位。
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开始,当男性写作在政治话语一端触礁,自然就带着失落、惆怅回到女人中间。他们在搞情趣、闹爱情中体验与官场同样的征服、委靡、痛苦。商业文化的娱乐性和作家精神的自恋需要交和在一起,生活之重轻松地消融在第二性崇拜的目光中。
新时期文学重回“五四”倡导的“人的文学”传统,以艺术的创造力探索更为深广的人生,这种创造力不应该仅仅表现在文章题材、结构方式的变化上,更应该体现在作家打量生活的新的精神境界中。当作家用文字的光亮照临世界的时候,这光芒应如萤火虫一样,即使很微弱,也足以给人类希望,因为它是勇敢燃烧自己的生命之火,是崇高的理想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