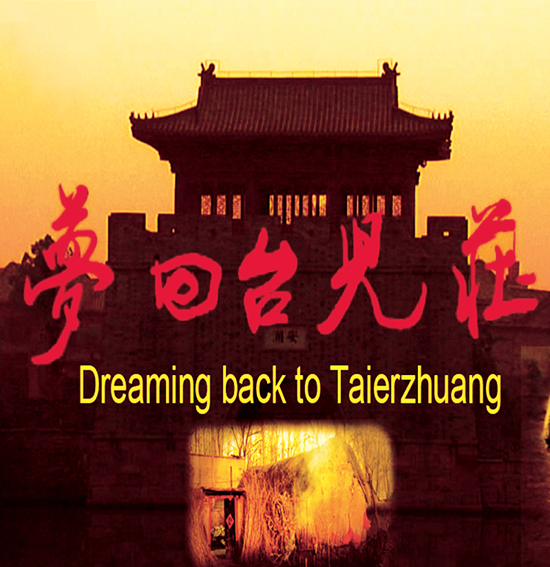
人在晚年容易怀念童年,人在异乡容易思念故乡,人若既在晚年又在异乡呢?那就一定会格外思念故乡的童年,或者童年的故乡。人类的这种情感特征,在由山民总编导的《梦回台儿庄》中得到了巧妙的运用。
片子一开头,是台儿庄古运河上明灭不定的渔火,接着响起一声连一声杜鹃的啼唤,声声似说:“快快归去!”然后,从遥远的天外飘过来有着浓郁的地方调式的民歌:“一只小船哟喂往南摇那个呢,半船那个葫芦半船那个瓢哟喂,半船那个红樱桃那个哎嗨嗨哟……”这一连串的声画符号,一下子就把人带入化不开的乡愁。这时,一个忧郁沧桑而明亮的解说声骤然响起:“七十多年了,多少次梦里回到我的故乡,而在梦的最深最深处,总是飘来一缕缕凄美的歌声……”主人公被设定为一位七十多年前为日寇的炮火所逼,漂泊海外的女性人类学家,而今她“不是不归归不得”,只能一声声诉说对故乡台儿庄的思念。
思念不是抽象的概念,思念是凝结在具象上的回忆和情感。于是片子里出现了一幅幅被岁月的流水浸蚀清洗过的民俗生活画卷:
燧石敲击出的火花、昏黄的油灯、缓缓转动的纺车、身穿印花布的少妇、摇篮里嗷嗷待哺的女婴;主人公童年时坐在油菜花中玩着“拾子儿”游戏;幼年时在荒凉的黑土地上拔草根喂驴驹儿;跟着大人在青青的麦浪中放风筝;冬日的暖阳中听老人唱民歌;元宵佳节刻萝卜灯,放刷帚灯;过端午节包粽子,插艾草;过年进古城听戏,看民歌民舞;故乡特有的“花棍儿舞”、“纤夫舞”、“人灯舞”、“柳琴戏”……
《梦回台儿庄》呈现的是一种节奏鲜明、充满色彩、辛苦却不乏乐趣的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它温馨而从容,自足而圆满。然而,这样的生活还在今天的台儿庄吗?
山民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他在拍摄该片过程中的艰难,因为没有人再用燧石击打火花,没有人再去转动吱呀吜吜的纺车,孩子们不再玩“拾子儿”的游戏,老人们也很少再唱民歌,而为了寻找一头耕地的牛他整整用了三天的时间……浪潮汹涌的工业化、城市化正在迅速地改变着农村的面貌,改变着农民们的生活方式,那些曾经真实、完整的一如在片中被编织的民俗生活图像,如今已经支离破碎得不成了样子。其实,只能用“梦回”的方式接近台儿庄民俗生活的,岂只是那个片中假想的主人公,至少还有山民自己!
在观看《梦回台儿庄》的过程中,我们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如果生活本身已经成为碎片,为什么还要克服重重困难力图呈现一种完整的假象?作为一个从那个年代里走来的人,山民无疑表达着一种怀旧的情绪。而在他的记忆里,民俗生活就是完整的。他用记忆编织的,虽是现实的假象,却是思想的真实。然而仅仅如此吗?难道这里面没有一种更深刻的反思吗?山民并不想传达一种保守的观念,因为他知道没有人能够阻挡住方兴未艾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潮流,城市的风景吸引着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土地,工业化的成果吸引着我们主动更新自己的生活。然而,离开了土地的生活真的就更幸福了吗?更新了生活方式的我们内心真的就更安宁了吗?在《梦回台儿庄》呈现的温馨、从容自足与圆满面前,我们真的觉得现实的生活没有缺失吗?在这个意义上,山民编导《梦回台儿庄》,其实并不是带领我们回到过去,而是当我们在现实面前感觉困顿的时候,提供一处慰藉和停泊心灵的安静港湾。
《梦回台儿庄》的总编导的山民,长期从事民俗研究与民俗学编辑工作,曾经担任《民间文化论坛》主编,自然深知民俗的这一功能,所以他把片子中的主人公设定为一位漂泊海外的人类学者,从人类学的视角去淘洗她浩如烟海的童年往事,从中选取那些最具民俗特征的画面,编织出了一条最能展示地域性格的民俗生活链。
很明显,这个片子是为宣传二战文化名城台儿庄的复建、呼吁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而制作的,但由于使用了民俗符号作为乡情的载体,在深层中就更具有强调民族认同,呼唤游子回归的力量。
同时,在笔者看来,虽然编导把这部片子定位为“民俗抒情片”,即主导思想不是展示民俗而是借民俗来抒发思乡爱国之情,但由于编导无意中对民俗的功能做出了形象的阐释,所以在民俗研究与民俗教学中,此片也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