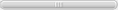听莫言讲故事,讲莫言的故事
黄河一样的莫言
□ 叶 子(福建青年作家)
也许从莫言站到斯德哥尔摩演讲台上的那一刻起,他将不得不背负上一块辉煌而又沉重的石头在这个世界上行走。莫言在纸上创立了一个高密东北乡的世界,这是他生命的决断,是他沉入少年世界的思辨与追忆,没有什么事物可以惊扰他内在的价值。莫言的根在于土地和母亲,他谈到给母亲迁坟的时候,母亲的骨殖和泥土已经融为一体——几十年了,莫言脚下的土地一直那样沉重,那样结实。斯德哥尔摩的演讲台上,我们很难从他穿着黑灰色中山装温和的外表、平静的声音里想象,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写出那么多暴力与诗意怪诞地纠集在一起的小说。乍一听他的演讲我们似乎恍惚看到一个穿着黄色土布的农民,和他的小说一样,初听初看也许让人有些失望,但只要你有耐心,你就会发现一些像骨头一样坚硬的智慧。
莫言曾经说过,长篇小说就应该像长江那么长,像黄河那么长。我个人觉得莫言作品的气质更接近于黄河,黄河的颜色更接近于土地的黄色。黄河里面泥沙俱下,黄河里的泥沙本身就是来源于两岸一路的土地。九曲黄河黄河九曲,有低沉的嘶吼,似隐隐的奔雷;涛声震天响,强壮的脉搏永远奔腾流淌,载重狂飙,经常决堤——鲜有冰封的时候,通常浊浪汹涌,黄水滔滔,似一条奔腾翻滚的黄龙,搅拌着浑浊的泥浆。天地苍茫,关山叠叠,黄河桀骜不驯,浩浩荡荡,骚动似铁蹄铮鸣。
莫言小说的风格就是黄河的风格。他的语言那么躁动、咸腥、粘稠、斑斓、跳跃,他一直在呈现人类从原始森林走到都市那尚未完全消失的野性,他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他力图呈现每个人心中那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他写作时身心俱用,五官迸张,他的《檀香刑》里描摹了无数酷烈的、令人身心俱裂的刑罚,这样的表达需要强大的心魄,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莫言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他的作品里充满原始生命的崇拜。直到上个月之前,我还坚持认为,相对于长江和黄河,我更喜欢长江,我喜欢长江的博大辽阔浩淼与平缓荡漾的绿波,它的下面有美丽的桃花鱼,如果水生物要建立一个水的王国,它们应该也更愿意生活在长江底下,而不是把它们的贝壳宫殿建立下浑浊的黄河之下。但一个月之后,在我认真读了莫言的小说之后,在我听过他的获奖演说之后,我动摇了我原先的想法。其实,黄河在巴颜喀拉山北麓发源初始,它也曾经拥有过长江那样的平静与清澈。黄河从青藏高原开始跋涉,一路汇集大小河流来者不拒,破崇山闭塞冲峡谷险恶,走南闯北迂回曲折越战越勇,一路漩涡、激流、瀑布奇景妖娆风驰电掣,全心系于龙门一刻终于向着渤海之滨滔滔东逝。
是的,浑浊正是蹉跎岁月的肤色,也是历史最本原的底色。莫言是一条冲突的黄河,童年时物质的匮乏与精神的丰饶二者之间构成无休止的敌意,他被自己推动着,不断改变途径和方向。在莫言的作品里,我觉得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一条河流。莫言在小说中开凿出一片名为高密东北乡、属于自己的历史岩层,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在这片以真实故乡广袤的乡村为背景充满想象力的岩层上展开并伸向历史的纵深处,而他则像一个草莽英雄在自己的王国里大口吃肉大口喝酒。黄河是无法模仿的,正像莫言具有范本意义但无人模仿一样。我的感觉在他演讲中的一句话得到验证:“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惊讶于他惊人的创作耐力与热情。他生命的分量就是小说分量的加码再加码,也许有人担心他被自己那些优秀的或者不那么优秀的作品所压垮,但我看着演讲台上的莫言,并没有看到他因为长期写作而显示出疲惫。可能有些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写得太多,自己擅长的、熟悉的写完了,就必须开始写自己不得不写的东西,思考自己不想思考的事物。目前为止,莫言是一个大胆快乐的写作者,但愿他不要变成一个郁郁寡欢的写作者。
莫言从未背叛过中国的写作传统,即使在他学习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技巧的时候,他也不曾彻底的背叛,他虽然曾经从东方走到西方,但他早早地醒悟到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是两座灼热的火炉,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最后莫言带着警惕之心再次回到东方,迫切地渴望一张属于他的东方的书桌。莫言往台上一站,故事张口就来,当他讲到最后一个故事的结局“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时,我通过视频清晰地听见一个现场听众发出抑制不住的会心的笑声。笑声说明这个故事是超出人的日常经验的,是让人听得津津有味的。莫言在演讲中回忆小时候因容貌丑陋被嘲笑欺负——作家往往是生活中的弱势,当一个鲜美的蛋糕端上来的时候,那些手脚伶俐的聪明人纷纷抢走一块蛋糕,等这些人一哄而散,笨拙的人才来到杯盘狼藉的现场,对着现场观察、记录、书写并且发呆,这个发呆的人最终成为了作家。
我觉得莫言即使以后写不出好的新作品,他这一生也已经足够,更何况他对未来充满野心和期待。他在处理历史题材的时候显得那样得心应手,但鲜见他对当下都市生活题材的尝试。他的写作愿望朝着历史扩张,与当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一空白地带可能是他写作上的盲点。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哪位作家没有自己写作上的盲点?也许这个任务等待下一个中国的莫言来完成。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作家无所不能,如果我们有这种愿望,那显然是一种无理要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莫言已经抵达一个终点。但是,他一定在等待,他在等那部在前方等待他的更伟大的小说。他左手夹着烟头,右手拿起笔开始写下未来的第一个字。当他站在演讲台上的那一刻,他四周的宇宙微微颤动了一下,然后迅速恢复了内部原有正常秩序的平静。很显然,他接过了瑞典学院颁发给他的这块石头,然后轻松地放了下来。
(编辑: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