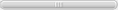伯格曼电影中的精神化时空——谈《野草莓》的创作特点
作为欧洲现代电影的旗帜性人物,英格玛·伯格曼一向秉承沉郁理性的精神,坚持简约质朴的影像风格,凭借其敏锐的生活洞察和丰富的镜头表现,使得他的电影有别于欧洲现实主义电影作者对当时社会生活的一般描写,在他的作品中习惯性地把摄影机指向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而探索人的精神灵魂,也正是这种运用影像手段探究人类精神命题的创作特质,成就了伯格曼“银幕哲学家”的美誉。
纵观伯格曼的电影作品,不难发现他的影片主题多为哲学命题,即通过对上帝的质疑、生死的探究以及对人性孤独的摸索,进而展开他充满困惑的哲学思辨,而这三个方面的银幕探索也构成了伯格曼电影世界不断追寻的三个基本主题。正如伯格曼自己所说,“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能够像电影那样,超越一般感觉,直接触及我们的情感,深入我们的灵魂。”也正是怀有这样的创作理念,才诞生了《野草莓》《第七封印》《假面》《芬妮和亚历山大》等一系列触及灵魂的经典,而跟随伯格曼的摄影机,也让当代人仿佛看到了剥去社会躯壳后那些赤裸而本真的每一个自己。在影像表现手法上,伯格曼擅于运用抽象的哲学概念去表达一种思想或精神状态,同时借助隐喻、象征、潜意识、梦幻等现代主义手法,在银幕世界里实现深奥的哲学探索。应当说,利用镜头语言构建精神化的时空体系,是伯格曼影像语言表达的鲜明特点。
这部拍摄于1957年的电影《野草莓》,镜头为观众展现了年迈孤独的伊萨克教授的精神之旅,但整个故事并不像《第七封印》那样在实际空间中展开合乎逻辑的顺序叙事,而是按照梦的逻辑来组织时空交错的旅程。用旅途表现人生,用梦境反思现实,是伯格曼电影最为常用的故事表现形式。应当说,伯格曼的很多创作灵感都来源于梦境,与其创作初期受到当时瑞典戏剧大师斯特林堡的熏陶影响不无关系,这也使得他的电影犹如一出梦幻剧,故事中梦幻与真实合乎情理地交错于银幕,也合乎逻辑地潜入人的内心意识。
其实,早在1946年伯格曼学生时代就推崇法国导演马赛尔·卡尔内的“诗意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并声称“电影应当走出现实主义,走出对人们周围的现实的描写”。在伯格曼的电影观当中,他认为幻想与真实没有明显的界限,电影应当成为想象和现实高度结合的载体。正如伯格曼自己曾经说,“我的电影从来就无意写实,它们是镜子,是现实的片段,几乎和梦一样。”也因此,他的创作想象可以自由驰骋,不受理性、顺序和时空的限制。可以说,梦不仅是他重要的剧作元素和表现手段,也造就了他的整体银幕形态和重要风格。
《野草莓》这部电影,标志着伯格曼梦幻剧电影观的彻底成熟,整部影片结构由四个梦组成,以噩梦开始、以美梦结束,形成环形剧作结构。梦不仅是伊萨克临终前回忆一生的心灵写照,也是影片组织结构的逻辑。这四个梦以伊萨克教授从斯德哥尔摩到隆德接受荣誉博士为故事主线,其间在旅程中穿插了老人触景生情后的一些片段回忆和梦境幻觉,在此伯格曼打破了时空的界限,让伊萨克在24小时内回顾和检讨了自己的一生。应当说,《野草莓》真正的功绩在于它创造性地建立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理式结构”。在这部影片中,现实与梦幻这两组时空内容保持着一种主题意义上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单纯叙事意义上的关系。也就是说,梦幻场面不再像叙事性闪回那样,单纯为了交代出现实故事的前史、以使观众知道剧情展开以前发生过什么,而是向观众揭示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生活,成为心灵的透镜。同时,梦幻时空的内容,又成为现实时空中人物行为的动力和依据,推动人物的性格发生变化。《野草莓》在欧洲电影史上之所以能够树立起一座影像叙事的里程碑,很大程度上缘于伯格曼的摄影机能够直接进入人的精神领域,并且形象地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变化过程,正是如此,伯格曼一直被视为“意识流”电影的教父级人物。
《野草莓》的开篇部分,宛如那部布莱松的《一个乡村牧师的日记》,以书信和日记的镜头进入到人物内心的描写。本片中伯格曼以伊萨克教授写日记的自述镜头作为影片的序言,进而展开梦幻剧式的故事。在伊萨克即将启程的那个早晨,老人做了一个噩梦,而这段梦境画面,也是迄今为止电影史上表现梦境的经典段落:没有指针的钟表、没有面部器官的行人、灵车在空寂的街道上孤独行驶、坠地的棺材中伸出一只手把自己往棺材里拉,棺材里的人竟然就是自己。这段超现实主义的梦幻镜头,利用强烈的明暗对比使光影交织成一片冷漠的几何形状,带给人一种神秘的恐惧感,仿佛具备了我们实际梦中的一切细节质感,增强了梦境的观影真实感。同时,这组超现实的银幕影调,多少都受到了意大利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契里柯的直接影响,并且在道具造型设计上能够找到类似于达利的无针软钟,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现代电影造型元素与美术观念发展的一脉相承。
在伊萨克和儿媳玛丽安的驱车途中,他们来到了伊萨克童年时代的夏日别墅,在别墅前面有一块草莓地,老人靠在一棵树下进入到了白日梦的幻境:在钢琴声与欢笑声交杂的背景环境音中,伊萨克看到了自己青年时代的恋人萨拉在摘野草莓。此时的梦境,好似传统叙事的闪回段落,但伯格曼并没有按照常规叙事手法安排青年的伊萨克与莎拉对话,而表现的却是年暮的伊萨克极力想与年轻的萨拉打招呼,但萨拉却视其如空气。这种穿越时空的闪回手法,阻隔了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不但使镜头的画面表现更似梦境,同时也在故事主题上突出了伊萨克晚年的孤独忧郁与痛苦无助。在旅程的后半段,玛丽安开车,伊萨克显得有些疲惫,不久就第二次进入到了白日梦:伊萨克回到了那片草莓地,摘完草莓的萨拉两次拿起手中的镜子让伊萨克面对自己的脸庞,并告知伊萨克“你知道太多,却不知道任何东西”。以此段落的梦境为始,伯格曼开始利用梦境闪回推动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当伊萨克面对镜中的自己时,其实已经在心理上开启了自知之旅,而萨拉的那段话在叙事上更宛若伊萨克的内心独白。应当说,让梦者深处梦境,但又无法参与梦境,这种闪回表现手法正是伯格曼为银幕营造精神化时空的功力所在。
在随后的旅途中,伊萨克教授目睹了阿尔曼夫妇的相互厌恶与相互攻击,从他们的身上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当年不幸的婚姻,可以说伯格曼在剧情上安排这对夫妇出现,也正是为伊萨克接受婚姻的“审判”而埋下的伏笔。在接下来的梦中,伊萨克来到了一个酷似审判庭的考场,随后他被带入一片树林。在密密麻麻的林间,伊萨克亲眼目睹了当年妻子与别人通奸的场景,而越轨之后妻子卡琳曾对着镜子哭诉,“他就像冰块一样冷酷,他的伪善让我恶心”。这番话也点醒了伊萨克一贯冷漠的神经,让他明白自己其实对于亡妻从未给予她所需要的关爱,甚至悔恨自己当时对卡琳的通奸行为都能无动于衷,痛苦之余他接受了妻子对他“自私”、“无情”的罪名控告,而判决的惩罚就是“和往常一样的孤独”。也正是在这个梦魇之后,老年的伊萨克开始清醒地认识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并为了能摆脱孤独、改善家庭关系而开始了自我拯救。在此后的时间里,伊萨克开始尝试与身边的家人重建感情联系,进而懂得关怀与给予,在付出关爱的过程中,也使得自己获得了精神上的慰藉与满足。
在伊萨克的最后一个梦中,初恋萨拉牵着他的手,穿过草丛来到河畔,远处垂钓的父亲和坐在旁边的母亲朝他挥手微笑,伊萨克亲切地望着对面的父母,整个画面恬静而富有诗意。伯格曼设计的这组镜头,充分展现了步入晚年的伊萨克与双亲在心灵上的接纳与和解,从而让主人公在精神上归于平静。当镜头转入现实场景后,躺在床上的伊萨克也终于露出了久别的笑容,从而为全片作结。整部影片,伯格曼安排伊萨克教授在一天内完成了一次人生的回顾之旅,剧作严谨缜密而又不乏张力:以接受有罪判决为因,以展开自我救赎为果;以接受个人荣誉为始,以懂得真心待人为终。
纵观伯格曼的所有影片,《野草莓》具备其电影作品的一贯风格,但又显得卓尔不群,该片曾在1958年柏林电影节上荣获金熊奖,并被电影界公认为伯格曼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从影片创作的角度来看,《野草莓》全片故事主题鲜明而又富有哲学意味,人物对白简短而又不乏内在表现力,剪辑节奏舒缓而又富有音乐韵律,影调平实质朴而又不乏高反差的明暗对比;从电影史的角度来看,应当说伯格曼在视听语言上的大胆尝试,启发和推动了现代欧洲作者电影的进一步革新,尤其对于法国新浪潮电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电影史上无愧为一部经典传世之作。如果说,伯格曼的电影犹如一面镜子,那么《野草莓》不仅照射出了我们的样子,也呈现了我们的灵魂。
(编辑:孙菁)
| 共1页 首页 | 上一页 1 下一页 | 尾页 转到第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