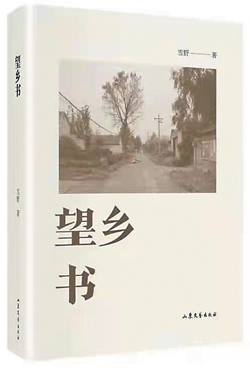
《望乡书》
雪野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21年3月出版
收到雪野寄来的散文集《望乡书》已有时日,它一直摆在我的案头,每天翻看,总有一段时光陷入沉思。今年的夏天来得有些晚,长长的“春季”是在有意让人回忆和留恋吗?我觉得是。
在长长的“春季”里读《望乡书》,我想是很相宜的,因为春愁与乡愁本来就是相通的。尤其是在这急剧变化的几十年,乡土也与春天一样,在人们的挽留与叹息中不断走远,恐怕最终只能“流水落花春去也”,空留愁绪在心头了。这部《望乡书》,正是一部写乡愁的书。作者的用心也是明显的,那便是事无巨细、不厌其繁地记下故乡的一切,让乡愁永远活在那个叫“西王善”的村庄的街道、树木、房舍、瓦砾和人物、故事里面,慢慢浸润在往后长长的日子里,不断地、长久地与人诉说。
于是,我们看到一切都在作者的笔下活起来了:西王善河东那棵树龄有五六百年的老槐树,树下那座毁于20世纪六七年代的关帝庙;那些吕氏的先祖,在历史上留下文名的吕传诰、吕宪瑞、吕宪春、吕宪和、吕宪秋、吕大声、吕大仕诸人;雪野的高祖、曾祖、祖辈、父辈和他记忆中的老屋,老屋前院子里的枣树和水井;他的父母的新家和新家里的动物们;村里的小河、石桥,村北的杏园,还有村子旁边的工厂。不只是这些,他还记下了那个小村中的婚丧嫁娶,记下了油条、包子、烤地瓜、爆米花、冰糕、橘子汁、西瓜、樱桃、板鸭、兔肉等美食,记下了一个少年眼里的人间苦涩;记下了他的小学、初中、高中生活,记下了他最初的文学启蒙和那些使他终生受益的师长。之后,雪野放眼他曾生活的那片土地,记下了那片土地上的麦子和玉米,长满了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韭菜、葱、长豆角、灰菜、苦菜的菜园,田野里、庭院里和村街旁的荠菜、薄荷、香椿、榆钱、槐花,还有推磨与推碾、刨麦茬、拾柴火、放羊等农活,看电影、看戏、捉迷藏、挖河蚌、捉知了、逮蚂蚱、做游戏等童年趣事。当然,还有那些神秘有趣的山野奇闻、日渐消逝的年节习俗,他的初恋和那些亲人们……
就《望乡书》内容的丰富性而言,我觉得它更像一部乡村史、家族史和个人自传,像一部简略的乡土志、风俗志和地理志,充满了温暖人间的烟火气息,焕发着童真和少年时代的生命活力。当然,这里既洋溢着无限的幸福,也渗透着无边的惆怅,因为正如雪野所说:“十九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家乡莱芜,对这里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十分熟悉,我最难忘的童年在这里度过,我最亲爱的人在这里生活,这些都深深地刻进了我的骨血、我的生命里。我对家乡,有言说不尽的深厚感情。 ”也正如雪野所感慨的那样,因为乡村城镇化,许多旧迹已经成为记忆,年轻人到外面闯世界,村子逐渐空心化,许多老房子坍塌了,荒草丛生。过去的许多东西都渐行渐远,引人深思。
这部《望乡书》还是一部怀想之书、悲悼之书,也是一部留恋之书、希望之书。他怀想过去的岁月是悲悼逝去的美好,他留恋逝去的美好是希望将来的回归。即便这种愿望无法实现,他也渴望在心灵一角留存一个精神的故乡。雪野写道:“人在年轻的时候,故乡是个地理概念;随着年龄增大,阅历增多,故乡会逐渐变为一种精神和观念的存在。‘此心安处是吾乡’,每个人都可以在心里建造一个自己认可的故乡,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场域,在这里丰富和完善自己,自由而有尊严地活着。 ”这个“精神故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重要而必需的,要不然我们真的都会变成无根之萍、无源之水,无处寄托自己的情感,安放自己焦虑不安、忧郁沉重的灵魂。我想,雪野的这种复杂情感既是个人的,也是我们大家共有的。他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的共同感受。我们可能思考得没有雪野那样深,也写不出雪野这样的文字,但在内心深处,却可以像他一样听到那一声声来自故乡、来自泥土的深情呼唤。
雪野是我的忘年好友,他在山东大学读书时我们就相识,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青年人的热情与活力,还有面对万事万物的清醒与镇定。他对那些美好的东西用情很深,对人间的丑恶也有一种天然的警惕,这些都让我喜欢,也给我很多启示。更为难得的是,他客居京华多年,依然初心不改。我想这与他酷爱读书、藏书有极大关系,是那些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思想、学术经典滋养和铸造了他的精神质地,使他慢慢地内化于心、发而为文,给我们这个社会奉献了温暖和美好、思虑与怀想。这样一个读书人、写作者,可能不会祈求走得很高,但一定会走得很远。将来,我愿意看他走到我望不见的远方,只把背影留下,让我长久凝望。
我还要一直把这本书放在案头,不时翻阅。因为我觉得,如果仅把回忆当作“回忆”、仅把乡愁看作“乡愁”,那显然是有负于雪野的这些文字和用心、用情的。留得乡愁与人说,我们从中看到的应该是一个关于人类未来的永恒话题,那就是质朴、纯粹、温暖与爱,还有对一个和谐美好社会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