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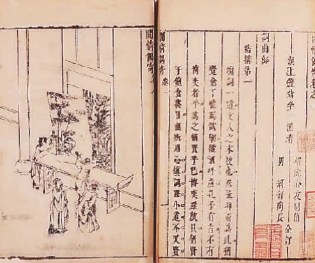
《闲情偶寄》
“窠臼不脱,难语填词! ”
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脱窠臼》中说:“窠臼不脱,难语填词! ”
其实,何止填词(戏曲创作)如此,一切艺术创造活动皆然。因为,在李渔看来求新是艺术的本性。李渔说:“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陈言务去,求新之谓也。 ”李渔一生的艺术创作也是不断求新的过程。他在《与陈少山少宰》中说:“渔自解觅梨枣以来,谬以作者自许。鸿文大篇,非吾敢道,若诗歌词曲以及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 ”
窠臼就是老俗套,旧公式,陈芝麻,烂谷子,用人家用了八百遍的比喻,讲一个令人耳朵起茧的老掉牙的故事。人们常说,第一个用花比喻女人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是蠢才。那“第二个”和“第三个” (庸才和蠢才)的问题,就在于蹈袭窠臼,向为真正的艺术家所不为。艺术家应该是“第一个” (天才) ,在艺术大旗上写着的,永远是“第一” !德国古典美学第一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上卷第46节至第50节中,关于天才说了许多惊世骇俗(今天看来也许有点极端)的话,但我认为十分精彩。他给天才下的定义是:“天才就是:一个主体在他的认识诸机能的自由运用里表现着他的天赋才能的典范式的独创性。 ”又说,“独创性必须是他的第一特性” ,“天才是和模仿的精神完全对立着的” 。这就是说,真正的艺术家(天才) ,创造性、独创性是他的“第一特性” 、本性;而“模仿” (更甭说蹈袭窠臼了)同他“完全对立” ,是他的天敌。艺术家必须不断创新,不但不能重复别人,而且也不能重复自己。在艺术家的眼里,已经存在的作品,不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都是旧的。李渔说:“非特前人所作,于今为旧;即出我一人之手,今之视昨亦有间也。 ”于是,艺术创作就要“弃旧图新” 。
在《闲情偶寄》中,李渔作为传奇作家特别强调传奇尤其要创新(卖“瓜”的王婆总离不开“瓜”乎) ,他认为“传奇”之名,就是“非奇不传”的意思。在他之前已有“非奇不传”之说,如明代倪倬《二奇缘小引》 “传奇,纪异之书也,无传不奇,无奇不传” (见倪倬《二奇缘小引》 ,载笔来斋刊本古吴许恒撰、倪倬校《初刻笔来斋订定二奇缘》 ,该文收入《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二,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383页) ;茅瑛《题牡丹亭记》 “传奇者,事不奇幻不传,辞不奇艳不传” ) ,而“新即奇之别名也” (见茅瑛《题牡丹亭记》 ,载明泰昌间朱墨套印刊茅瑛批点本《牡丹亭》 ,该文收入隗芾、吴毓华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 ) ,而且一有机会李渔必张扬创新。在《宾白第四》中他又倡“意取尖新” :“同一话也,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有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意懒心灰,有如听所不必听。白有尖新之文,文有尖新之句,句有尖新之字,则列之案头,不观则已,观则欲罢不能;奏之场上,不听则已,听则求归不得。 ”
当然,创新也不是不要传统,而是继承中的革新。李渔在《格局第六》的前言中批评了“近日传奇,一味趋新,无论可变者变,即断断当仍者,亦加改窜,以示新奇”的不良倾向,将创新与继承联系起来。
但是,新奇又绝非“荒唐怪异” ,而须“新而妥,奇而确” ,即符合“人情物理” 。关于这一点,李渔在《戒荒唐》一款中有相当透辟的论述。
“新”与“旧”的辩证法
关于创新,李渔自有其独到见解,所谓“意之极新者,反不妨词语稍旧,尤物衣敝衣,愈觉美好” ( 《窥词管见》第六则) 。
这是“新”与“旧”的辩证法。
李渔所重,乃“意新”也。倘能做到“意新” ,词语不妨“稍旧” ,所谓“尤物衣敝衣,愈觉美好” 。这使我想起明代杨慎《词品》卷之三“李易安词”条一段话:“ (李易安)晚年自南渡后,怀京洛旧事,赋元宵永遇乐词云:‘落日熔金,暮云合璧。 ’已自工致。至于‘染柳烟轻,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 ,气象更好。后叠云:‘于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 ’皆以寻常言语,度人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妙者难。山谷所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者,易安先得之矣。 ”杨慎以李易安词为例,形象解说了“精巧”与“平淡” 、 “故”与“新” 、“俗”与“雅”的辩证关系。
这里既有一个各种关系之内外表里辩证结合的问题,也有一个孰轻孰重的问题。我是说,词人应该多做“内功” ,要从根柢下手。创新的功夫,根本是在内里而不在表层,在情思不在巧语。创新的力气应该主要用在新思想、新情感、新感悟的开掘上,而不是主要用在字句的新巧奇特甚至生僻怪异上。
当然,内里与外表、情思与巧语、意新与字(句)新、内容与形式等等,又是不可决然分开的。一般而言,常常是新内容自然而然催生了新形式,新情思自然而然催生了新词语;而不是相反。文学艺术中真正的创新,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人工“做”出来的。
总之,功夫应该从“里”往“外”做、从“根”往“梢”做。这样,创新才有底气、才深厚、才自然天成,作品才能使人感到“新”得踏实、“新”得天经地义、“新”得让最挑剔的人看了也没有脾气。这即第七则开头所言:“琢句炼字,虽贵新奇,亦须新而妥,奇而确。妥与确,总不越一理字,欲望句之惊人,先求理之服众。 ”任何文学样式——诗词古文小说戏曲等等,其创新必须有这个“理”字约束、管教。 《红楼梦》中生在诗书之乡、官宦之家的贾宝玉偏偏厌恶仕途经济,在当时够新奇、怪异的,但他并不背“理” ——不违背大观园那个典型环境里的“人情物理” 。
耳目之前与闻见之外
李渔在为他朋友的《香草亭传奇》作序时提出,创作传奇必须“既出寻常视听之外,又在人情物理之中” 。在《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 “戒荒唐”中又说:“凡作传奇,只当求于耳目之前,不当索诸闻见之外。 ”李渔坚决反对以荒诞不经材料的手段创作传奇。尤侗眉批:“昔人传奇,今人传怪矣。笠翁此论,真斩蛟手! ”
的确,李渔所言,可谓至理名言!
在艺术创作中,新奇与寻常、“耳目之前”与“闻见之外” ,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因为“世间奇事无多,常事为多;物理易尽,人情难尽” 。而那“奇事”就包含在“常事”之中;那“难尽”的“人情”就包含在“易尽”的“物理”之中。若在“常事”之外去寻求“奇事” ,在“易尽”的“物理”之外去寻求“难尽”的“人情” ,就必然走上“荒唐怪异”的邪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寻常生活本身永远会有“变化不穷”“日新月异”的奇事。戏曲作家就应该寻找那些“寻常”的“奇事” 、“真实”的“新奇” 。
三百多年前李渔对新奇与真实的关系有如此辩证的认识,实属难得。
明末清初在戏曲创作和理论上存在着要么蹈袭窠臼、要么“一味趋新”的两种偏向。陈多先生在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注释本《李笠翁曲话》中解释《脱窠臼》时,引述了明末清初倪倬《二奇缘小引》 、茅瑛《题牡丹亭记》 、张岱《答袁箨庵(袁于令)书》 、周裕度《天马媒题辞》 、朴斋主人《风筝误·总评》中的有关材料,介绍了他们对这两种倾向、特别是“一味趋新”的倾向的看法。有些人的意见与李渔相近。例如,张岱批评说,某些传奇“怪幻极矣,生甫登场,即思易姓;旦方出色,便要改装。兼以非想非因,无头无绪。只求热闹,不论根由;但要出奇,不顾文理” ;他认为“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传之久远。愈久愈新,愈淡愈远” 。周裕度说:“尝谬论天下,有愈奇则愈传者。有愈实则愈奇者。奇而传者,不出之事是也。实而奇者,传事之情是也。 ”朴斋主人指出,“近来牛鬼蛇神之剧,充塞宇内,使庆贺宴集之家,终日见鬼遇怪,谓非此不足以悚夫观听” ;“讵知家中常事,尽有绝好戏文未经做到” 。他认为,传奇之“所谓奇者,皆理之极平;新者,皆事之常有” 。可以参考。
说“尖新”
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宾白第四》 “意取尖新”款云:“纤巧二字,行文之大忌也,处处皆然,而独不戒于传奇一种。传奇之为道也,愈纤愈密,愈巧愈精。词人忌在老实,老实二字,即纤巧之仇家敌国也。然纤巧二字,为文人鄙贱已久,言之似不中听,易以尖新二字,则似变瑕成瑜。其实尖新即是纤巧,犹之暮四朝三,未尝稍异。同一话也,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有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意懒心灰,有如听所不必听。白有尖新之文,文有尖新之句,句有尖新之字,则列之案头,不观则已,观则欲罢不能;奏之场上,不听则已,听则求归不得。尤物足以移人,尖新二字,即文中之尤物也。 ”
大家看到,李渔在这里竭力鼓吹戏曲作家应该注意遣词造句时选取“尖新”字眼儿。“尖新”虽是李渔在论
宾白时提出的要求,其实它何尝不适宜于唱词?李渔所谓“尖新” ,是对“老实”而言。所谓“尖新”者,一方面是指语言要新鲜而不陈腐,另一方面是指语言要生动活泼,富有表现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李渔之“尖新” ,含有王骥德之“溜亮”“轻俊”“新采”“芳润”等意思在内,趣味十足,令人眉扬目展。好的戏剧,其语言都应该是“机趣”“尖新”的。例如老舍《茶馆》第二幕中一段台词,唐铁嘴对王利发说:“我已经不抽大烟了! ”王利发对此很惊讶:“真的?你可要发财了! ”接下去唐铁嘴的台词可谓“尖新”“机趣” :“我改抽‘白面’啦。你看,哈德门烟又长又松,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 。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 ,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 ”再如,关肃霜主演的京剧《铁弓缘》 ,许多台词也很有机趣,可称尖新。剧中老太太回答那个官宦恶少求婚时说:“蚊子叮了泥菩萨——你认错人了! ”这是一句歇后语,用在这里十分贴切,令观众开怀、捧腹。
“把我掰碎了成你”
由“尖新”我想到了艺术的继承和创新,想到了现代戏曲艺术家袁世海和他的老师郝寿臣。
袁世海当年拜郝寿臣为师,郝寿臣问:你准备怎么跟我学?是把你掰碎了成我,还是把我掰碎了成你?袁世海说:把我掰碎了成你。郝寿臣说:那不行,那样你就不是袁世海了,而成了袁寿臣了;我也有缺点,不能连缺点什么都拿去,而是把我好的东西拿去。所以,不是要把你掰碎了成我,而是要把我掰碎了成你。
后来,袁世海收杨赤为徒,也把当年郝寿臣对他说的那番话对杨赤说了,要杨赤把自己掰碎了成为杨赤(据2002年12月24日中央电视台1套《东方时空》袁世海专集) 。
郝寿臣、袁世海这些中国艺术大师的话,使我想起英国十八世纪著名诗人爱德华·扬格《试论独创性作品》中反复阐述的一个思想:“学习大师是为了成为你自己” ,“对著名的古人,我们越不模仿他们,就越像他们” 。扬格说:“让他们(古典大师)滋养而不是消灭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读书时,让他们的优点点燃我们的想象;我们写作时,让我们的理智把他们关在思想的门外。连对待荷马本人,也要像那位玩世不恭者对待崇拜荷马的君主一样:叫他站开点,不要挡住我们的作品,使它受不到我们自己天才的光芒的照耀;因为在别的太阳光下,没有什么独创性的东西能够生长,没有什么不朽的东西能够成熟的” (爱德华·扬格《试论独创性作品》第86页,袁可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当然,听扬格的话,你会觉得太不“中国”了——没有中国传统艺人那种亲如父子的师生情谊,那种舍身为人的高尚情怀。然而,理儿还是相通的。
而且,这个理儿管得很宽,人类要想生存、要想发展,一切事业和所有个人都要归顺在这个理儿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