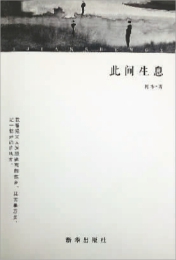
《此间生息》 阿零 著
新华出版社 2016年3月出版
两年前,阿零给我发来她的小说片段,我说,这不是萧红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吗?
数周前,我在千里之外一个寂静村庄的小河边,阅读到完整版的短篇小说集,感觉阿零和萧红还是不一样。萧红笔下的乡村,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而阿零笔下的故乡,人不慌不忙地生,不慌不忙地死。萧红对故乡的记忆,如血滴在雪地里,雪白血红,如她31岁的人生。阿零对故乡的记忆如水滴在水里,死是生的一部分,不慌不忙,如她温婉的一个回眸。
故乡,离得越远,离开的时间越长,她越清晰,清晰到有些晃眼,围着每一个晃眼的光点,他们变成故事,铺陈在阿零的笔下。 《饥饿的寡妇》中的寡妇、 《我要娶美珍》里的阿憨、 《药》里的美珠阿姆,甚至是死刑犯秋生,每一个人,她都温柔对待。
那些曾经的挣扎、恐惧、无奈、抗争,都是无效的,最后他们不得不选择麻木或者偏执,最后无声无息地流逝。他们的灵魂一直在漫无目的地游荡,那样孤独无依。阿零在喧嚣的都市中,一天天为那些灵魂不安起来。没有一所房子将他们安顿下来,她便放不下心。她键盘下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块砖瓦,她的书变成一个容量巨大的房子,房子里有生死两隔的爱人,有外婆温暖的后背,有吃不完的粮食,有明亮的灯光,有希望,有爱……
“我曾经义无反顾逃离的故乡,其实是原点,是一切开始的地方。 ”阿零在封面上这样写。作为一个写作者,阿零“回”到故乡,我由衷地为她高兴。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是离得开故乡的。福克纳说:我的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是值得好好描写的,而且,即使写一辈子,我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莫言就直言不讳地说他受到福克纳的影响。因此他笔下的故乡高密东北乡为他盛产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并把他送到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现场。还有马尔克斯的马贡多、沈从文的湘西边城、大江健三郎的北方四国森林、杜拉斯的湄公河岸……
我理解阿零的“逃离”又“回归” 。正如莫言在《小说的气味》中写道:出生在中俄界河乌苏里江里的大马哈鱼,在大海深处长成大鱼,在它们进入产卵期时,能够洄游万里,冲破重重险阻,回到它们的出生地繁殖后代。对鱼类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我们不得其解。近年来,鱼类学家找到了问题的答案:鱼类尽管没有我们这样突出的鼻子,但有十分发达的嗅觉和对于气味的记忆能力。就是凭借着这种能力,凭借着对它们出生的母河的气味的记忆,它们才能战胜大海的惊涛骇浪,逆流而上,不怕牺牲,沿途减员,剩下的带着满身的伤痕,回到了它们的故乡,完成了繁殖后代的任务后,就无忧无怨地死去。母河的气味,不但为它们指引了方向,也是它们战胜苦难的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马哈鱼的一生,与作家的一生很是相似。作家的创作,其实也是一个凭借着对故乡气味的回忆,寻找故乡的过程。
那些“灵魂”住进了阿零建构的房子里,她说写完就感觉像一件心事已了,可以离开。相信,有一天,她会再次踏入那间房子,与那些灵魂做一次次的深谈,那时,她的小说将唤起更多人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