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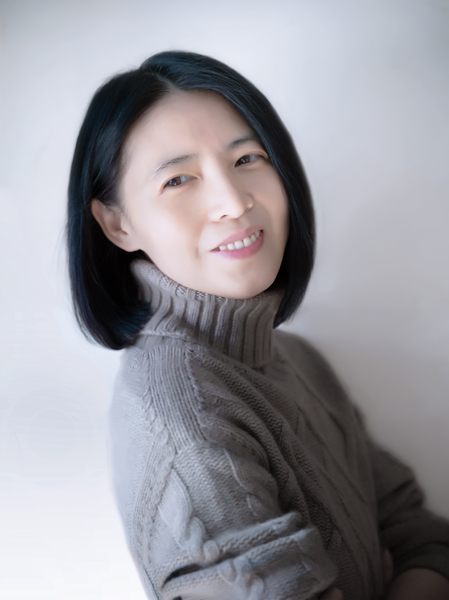
张萍
让“身体”消失——始于“女性舞蹈”艺术的学科关怀
论坛的主题是女性艺术与艺术女性,如果缩小光圈把关键词换成舞蹈,“女性舞蹈”与“舞蹈女性”作为关照对象,某种程度上讲,“身体性”必然成为重要的破题视角,甚至是重构新时代女性舞蹈艺术底层逻辑的关键一环。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妨先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听到“舞蹈”两个字,脑海里立马浮现出来的形象是什么?或者更简单一点是男是女?如果说对这个结论有所迟疑,我们换个问题,假如“推荐亲戚或朋友家的孩子学跳舞”男孩和女孩、胖和瘦、五短和修长、大头和九头身?您怎么选?我想大多数人的判断是有基本共识的,体现为两方面的数据:一是报考舞蹈院校(无论哪个专业),筛选比率女性通常是男性的数倍级;二是社会各类舞蹈培训班悬殊的性别比。但是也有反例,比如街舞、爵士舞班,男女比例甚至会倒置,是不是可以简单推测为,舞蹈艺术的“身体性”本质,造成身体被前置,处于高度“展示”状态,于是一种舞蹈样式到底强化性征还是弱化性征会成为重要的选择因素?
按照海德格尔《林中路》提出的,艺术的基本存在方式,首先是“质料”(物料)的存在,即任何艺术作品都是通过具体的物质载体(即介质)呈现的,舞蹈艺术同理,但又极为特殊,它的介质就是人的身体,当然,我们讨论的不是广义的自娱性舞蹈,而是纳入表演艺术范畴的舞蹈,这时候的基本载体通常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的身体,而是经过技术性改造的“专业化”身体。无论是风格性(文化属性)、功能性还是技术性改造,背后都有着共同的驱动力——身体审美权力,在穿越不同的人类文明形态过程中,这个外置“目光”长期作用于舞蹈样态的走向。例如,在不同朝代不同地区的画像砖石、石刻、壁画、文物等造型艺术中呈现的乐舞形象,多“三道弯”形态,史书典籍也记载着“舞柳腰”“舞腰回雪”“舞腰肢软”“舞腰无力”“舞腰蜂细”“舞腰新束”“腰肢纤细”“沈腰消瘦”等软、曲、轻的女性身体审美特征。这一重要审美形态的背后是官方与民间交互、渗透,共同作用的结果,始自上古三代的整个前现代文明时期,诸如“乐府”“清商署”“教坊”“瓦里”这类专事乐舞的官方机构主导着雅、俗乐舞身体审美的世俗化走向。以腰为中心点的“S”型运动形态,不仅使腰、胸、臀成为视觉显著点,而且进一步强化着胸、腰、臀的比例反差,“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对女性身体物化、性化、异化的至高权力,决定着传统乐舞在传统男权社会“娱人”“欲人”的功能定位。无独有偶,形成于欧洲宫廷的世界经典舞蹈艺术样式“芭蕾”,也体现着“身体”的女性审美。芭蕾艺术独特的技术规范:外开、直立,从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同步向外旋转90度,如果就形态的生理性暗示与想象而言对女性并不友好,但却能够带来轻盈、飘逸、优雅、流畅的腿部姿态;事实上,外开只是第一步,始于浪漫主义芭蕾《仙女》的足尖鞋,女性舞者的“趾立”(足尖)技术不仅带来极高的技术审美,更提供了一种对女性理想身体的想象,超黄金比律的上下身比例,但也因无法产生持续动力,形成依附性的双人舞技术,表现为男性主导与控制的“把位关系”……
鲍德里亚关于“女性及女性身体被赋予作为美丽、性欲、指导性自恋的优先载体”的论断,佐证了舞蹈艺术“身体”的女性化审美是有着来自传统男权社会复杂的历史根源的。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舞蹈艺术必须要纳入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框架中,这一点不置可否。那么问题来了,面对审美权力建构下的身体性审美,谈“女性舞蹈”如何取舍?难道是对经过人类历史优选的传统舞蹈文化进行一次清零?或许,一百多年前伊莎多拉·邓肯领衔发起的“现代舞”的身体革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洛伊·富勒、露易丝·圣·丹尼斯、玛莎·格莱姆、多丽丝·韩芙莉,玛丽·魏格曼等一批女性舞蹈家,继邓肯发出“芭蕾一点也不美”的昭告之后,纷纷自立风格、原则、标准,舞台上暗涌着现代哲学思潮的潜流:平权思想、人本主义,对人、对身体的异化的反抗……她们任由哺乳期的身体,射出一道道与古典芭蕾所有的审美原则背道相驰的箭,尝试以一种技术性建构取代另一种技术性建构,以期全面改造身体形态,实现对传统审美权力的反拨。可是,现代舞蹈艺术家的努力,并没有改变芭蕾艺术几百年来光照的世界。
我想那场革命或许是一次解放但不是新生。事实上现当代艺术本体在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中经历着多次转向,不断攀向更高的思想境界、精神价值与美学追求。今天舞蹈艺术的立场、内涵、目标、任务、使命与传统舞蹈艺术不可同日而语,作为“身体的艺术”,舞蹈不再是身体的展示性艺术,而是表达性艺术,当再次让身体从艺术载体越位为艺术表达时,只能将舞蹈艺术带离跑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故而不是紧盯被男权规训或是被女权放飞的“身体”,而是要让身体“消失”,回归人本身,展现人的主体性与精神价值。让身体消失绝不是舞蹈文化的消失,传统舞蹈文化资源既体现为蕴含着舞蹈审美法则的丰富素材,又体现为蕴藏着身体表达法则的经典艺术剧目,是对当下舞蹈艺术进行身体建构、审美建构与思维建构的沃土。纳入学科体制的当代中国舞蹈艺术,即是建立在中西方传统舞蹈文化资源基础之上,按照舞种思路探索学科体系化道路的,早期实践的三大舞种: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与西方芭蕾舞,都是深植传统舞蹈文化土壤,至今仍位列学科顶端的霸主。可见舞蹈艺术的发展恰恰是离不开传统舞蹈艺术的滋养。只是既有的学科教育更多地表现为关照舞蹈身体和舞蹈审美有余,对舞蹈思维的建构明显不足。
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舞蹈”议题,对推动当代舞蹈艺术系统的学理建构有着积极的作用。众所周知,任何一门艺术都比较容易切分介质、技术、素材、手法、审美属性、规律与作品之间的边界,就像音乐同小提琴、电影同胶片或摄像机、文学同文字之间,隔着技术、素材、手法、审美属性、艺术规律等一系列复杂的结构层级……可舞蹈之所以特殊,是由于介质太特殊了,各种反自然的技术规范,需要在未成年阶段开启系统的训练,譬如成百上千次Battement 腿部与脚部的训练组合、Port de bras 舞姿组合……无论是功能性、技术性、风格性,对身体介质的系统性改造,离不开复杂的训练体系、表演风格体系、经典剧目体系(创作体系)三者的叠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仅舞者自觉地建构完成了对身体的审美认同,三个体系彼此间也是水乳交融,一方面不断丰富着既有的舞蹈文化资源,是重要的素材积累与建设的过程,另一方面当素材经过有效组织通过专业化的身体呈现时,已经具备“准作品”形态了,甚至具有较高的形式审美价值。长此以往,“身体”被高度前置,身体与建构身体的舞蹈资源(素材)长期“粘连”,造成了一种误读:当舞蹈作为个体生命情感的自由表达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身体即是舞蹈;当“人体”作为抽象的艺术符号,去创造一个形式表达系统时,素材即是舞蹈。原本素材必须经由主体创造的“表达法”变成有效的形式表达系统,再通过介质呈现的“舞蹈”链条,被打破、取消甚至驱逐。从而导致大部分编导很难捕捉到有效的“舞蹈身体表达法”,致使身体作为艺术符号去表达思想的艺术性原则遭到减损与剥夺。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人们对于舞蹈艺术依然存在某种性别偏见。因为太多的舞蹈作品,一直陷入“身体”的展示性特点和“动作”的表达性需求的拉锯战中,“身体”的意义和审美价值不能确立为有效表达人的情感、思想和精神价值的艺术符号,从而一次次沦为 “纯展示”的境地。
“女性舞蹈”再次将舞蹈的“身体性”问题抛到台前,给了舞蹈艺术一次端正学科逻辑起点的机会,在舞蹈艺术内需要解决的问题层面或许比较低,需要先在技术或艺术范畴的层面,解决“how”即怎样表达的问题。但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没有立足于女性立场的身体性、情感性与意识性的“女性舞蹈”艺术,恰恰相反,例如以舒巧、王玫等为代表的女性舞蹈艺术家,她们在舞蹈舞台上,借经典文学形象重新定义的三毛、玉卿嫂、繁漪、甄宓等女性艺术形象,不再保有被男性审美筛选过的女性品质,可以说是一种大胆的赋予,甚至是对传统审美权力的挑衅与颠覆……体现出创作主体的思想价值与精神高度。当然作为优秀的女性编导家,二者无疑是可遇而不可求,可盼而不可及的。
面对当下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新审美权力带来的“耽美式”“女性化”“技术化”“视觉化”的趣味与走向,谈“女性舞蹈”的话题,展开对舞蹈的身体性问题的新一轮思考,其意义已经超出性别主体意识或意志。舞蹈不仅是身体的艺术,更是人的艺术,必须回归“人”的主体性,回归身体与艺术表达之间的路径建构,从而才能真正实现舞蹈艺术独有的审美价值,也才能真正体现一门艺术坚守人民性、主体性、民族性、时代性、价值理性的使命与担当。
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舞蹈》杂志执行副主编(编审)。曾出版及发表多部理论专业书籍及文章。代表作:《中国舞蹈著作权现状及对策研究》《危险的缺失》《谁来振动一下舞蹈》《怀着向往“经典”之心——当代舞蹈创作的美学维度及其结构形式策略反思》》等。与他人合著《中国舞蹈名作赏析》《中外舞蹈精品赏析》。曾获中国文联理论评论奖及中国舞蹈“荷花奖”理论评论奖等国家级文艺理论奖项。